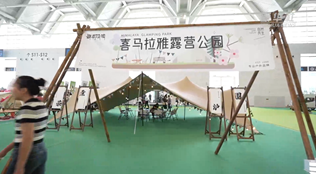“少年時(shí)尋見(jiàn)光,青年時(shí)遇見(jiàn)愛(ài),暮年到來(lái)的時(shí)候,你的心依然遼闊。一生追隨革命、愛(ài)情、信仰,輾轉(zhuǎn)于戰(zhàn)場(chǎng)、田野、課堂,人民的敬意,是您一生最美的勛章。”
這是《感動(dòng)中國(guó)》組委會(huì)給予一位老人的頒獎(jiǎng)詞。老人名叫龔全珍,是開(kāi)國(guó)少將甘祖昌的夫人,也是全國(guó)道德模范、“最美奮斗者”稱(chēng)號(hào)獲得者,被習(xí)近平總書(shū)記親切地稱(chēng)為“老阿姨”。她追隨丈夫扎根革命老區(qū),成為一名普通的教師,教書(shū)育人、無(wú)私奉獻(xiàn)。
9月2日16時(shí)16分,龔全珍老人因病醫(yī)治無(wú)效逝世,享年100歲。
去世前,這名已有71年黨齡的老人,雖然身體大不如從前,可她始終認(rèn)為,自己是名黨員,就應(yīng)該天天用黨員的標(biāo)準(zhǔn)要求自己,恰如她在日記中所言——
“殘荷,雖失去春夏時(shí)的風(fēng)采,卻堅(jiān)持挺住,不怕秋風(fēng)的襲擊,它要把最美好的東西留給人們,在挖出一擔(dān)擔(dān)潔白的蓮藕時(shí)才倒下,它奉獻(xiàn)了一生,人也該有這種精神。”
這是龔全珍發(fā)自肺腑的心聲,也是她人生的寫(xiě)照。
“義無(wú)反顧踏上了自己的路”
“我的一生像棵小樹(shù),童年在日本帝國(guó)主義和國(guó)民黨統(tǒng)治下雖幸得保住生命,但先天不足無(wú)力長(zhǎng)成參天大樹(shù),卻也能在森林中做出自己的一點(diǎn)點(diǎn)綠色,保持綠色直到回歸自然。”
——摘自2008年10月2日龔全珍日記
今年夏天,記者來(lái)到南昌大學(xué)第一附屬醫(yī)院象湖院區(qū),探訪病床上的龔全珍。
在一份診斷書(shū)上,醫(yī)生密密麻麻地給她列出了尿毒癥、心功能不全、高血壓病等多種疾病,但當(dāng)時(shí)的她仍然笑容慈祥。
回顧人生,龔全珍說(shuō)自己是幸福的:“人生,各自選擇自己的路。我選擇物質(zhì)生活簡(jiǎn)陋,而精神生活充實(shí)的路,生活會(huì)愉快些、幸福些。”
醫(yī)院里,半夢(mèng)半醒間,她的思緒常常回到熟悉的校園,有時(shí)把醫(yī)護(hù)人員認(rèn)成自己的學(xué)生:“孩子們別在這逛來(lái)逛去,趕快去上課,記得要好好讀書(shū)。”
即使是在病中,老人的心也總裝著別人。
有一次,聽(tīng)到醫(yī)生說(shuō)要給她抽血化驗(yàn),病床上的她以為要獻(xiàn)血,便強(qiáng)打起精神說(shuō):“我是O型血,是萬(wàn)能血型,誰(shuí)都可以用,你們隨便抽多少都可以。”
5年前,記者采訪龔全珍時(shí),老人精神矍鑠,回憶起往事,總是掛著淡淡的笑容。她說(shuō),數(shù)十年來(lái),自己花了很多時(shí)間寫(xiě)東西,寫(xiě)的最多的還是甘祖昌的故事。她把《我和老伴甘祖昌》一書(shū)贈(zèng)予記者,其中記錄了他們夫妻倆走過(guò)的風(fēng)雨歷程:“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,沒(méi)有寫(xiě)好,怕對(duì)不起讀者。但書(shū)里的每一個(gè)字,都是用心寫(xiě)出來(lái)的,每一件事,也是真實(shí)有據(jù)的。”
據(jù)龔全珍介紹,她出生在山東省煙臺(tái)市一戶工人家庭,兄弟姐妹11個(gè),過(guò)著清貧的生活,記憶中的家“巷子邊有一條大馬路,可直通到海邊”。
兄弟姐妹中,龔全珍最崇拜三哥。
1938年初,日軍侵占煙臺(tái)。三哥參加了八路軍。還在讀小學(xué)五年級(jí)的龔全珍拉著三哥的手,央求說(shuō):“哥,帶我去吧,我也要當(dāng)八路打鬼子。”
“你還小,好好讀書(shū),過(guò)三年我回來(lái)領(lǐng)你參加革命。”三哥說(shuō)完,背上包就走了。
三年后,龔全珍考上煙臺(tái)市立女中上高一,可三哥依然杳無(wú)音信。那時(shí),日軍只要占領(lǐng)了一處地方,就會(huì)下令叫學(xué)生集合開(kāi)慶祝會(huì)。學(xué)校校長(zhǎng)指定龔全珍當(dāng)市立女中的代表,她很不情愿。
散會(huì)后,教育局的官員又帶著中小學(xué)生代表去給日本兵送慰問(wèn)金。
進(jìn)了憲兵隊(duì)的大門(mén),龔全珍看到這些殺害中國(guó)同胞的劊子手,還有用中國(guó)人的血肉養(yǎng)活的狼犬狂吠著,她感到頭皮發(fā)麻,全身發(fā)抖。
她永遠(yuǎn)忘不了,一個(gè)大雪紛飛的日子,一位老鄉(xiāng)因帶半袋鹽,被日本兵扒光衣褲,用刺刀割開(kāi)后背的皮肉后,把鹽撒了進(jìn)去,血流了一大片。
從憲兵隊(duì)回到家后,龔全珍徹夜難眠,她不想當(dāng)亡國(guó)奴,于是下定決心離開(kāi)煙臺(tái),去日軍還未踐踏過(guò)的地方,“如果打聽(tīng)到三哥的消息,我就有機(jī)會(huì)當(dāng)八路,為死難的同胞報(bào)仇雪恨”。
18歲的龔全珍剪短頭發(fā),從煙臺(tái)步行到濟(jì)南,再輾轉(zhuǎn)安徽阜陽(yáng)、河南淅川直至落腳陜西城固,一天最多能走100多里路,這是流亡路上練出來(lái)的本領(lǐng),“沿途的人把我們當(dāng)成叫花子”。
龔全珍一路流亡,一路求學(xué)。那時(shí),西北大學(xué)南遷至城固縣城。龔全珍報(bào)考了西北大學(xué)教育系,并以?xún)?yōu)異的成績(jī)被錄取。
陜西省檔案館至今保存著一份龔全珍入學(xué)時(shí)填寫(xiě)的《國(guó)立西北大學(xué)新生調(diào)查表》。其中,“思想”一欄“對(duì)于國(guó)家現(xiàn)狀之感想及將來(lái)希望”中,她填寫(xiě)道:“政治紊亂,國(guó)民教育至今不能普及,希望國(guó)家能樹(shù)立一個(gè)真正為人民福利著想的政府,希望提高教育水平。”
1949年,即將畢業(yè)的龔全珍思考著自己的出路。恰在此時(shí),時(shí)任西安軍管會(huì)主任的賀龍來(lái)到西北大學(xué),他號(hào)召同學(xué)們參軍建設(shè)西北。
龔全珍很受鼓舞,當(dāng)即報(bào)名參軍,實(shí)現(xiàn)了戎裝夢(mèng),成為一名解放軍戰(zhàn)士,被分配到新疆軍區(qū)八一子弟學(xué)校當(dāng)老師。
次年春天,楊柳已發(fā)出嫩綠的葉子。龔全珍和100多名同行的青年爬上卡車(chē),高唱著軍歌向新疆進(jìn)發(fā)。
似亭亭凈植的荷花,龔全珍毅然決然踏上了為之奮斗一生的革命之路。
“愛(ài)自己所愛(ài),無(wú)怨無(wú)悔”
“他雖不像知識(shí)分子那樣溫情,他愛(ài)得灼熱,他承認(rèn)我為他付出的一切。我們也有共同之處,對(duì)生活要求不高,為理想可以貢獻(xiàn)出一切。”
——摘自1988年12月21日龔全珍日記
她和他,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起點(diǎn)。
他于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鄉(xiāng)市蓮花縣一個(gè)叫沿背的小山村。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后,他不得不輟學(xué)回家,放牛、打草,挑著擔(dān)子來(lái)回走幾十里山路,掙幾毛錢(qián)腳力費(fèi)維持全家生計(jì)。此后,他參加過(guò)長(zhǎng)征、抗日戰(zhàn)爭(zhēng)、解放戰(zhàn)爭(zhēng)……曾多次負(fù)傷,革命足跡遍布大半個(gè)中國(guó)。
從贛西農(nóng)村到膠東半島再到天山腳下,兩條相隔千里的生命軌跡,竟然神奇地交織在了一起。
1952年冬天,龔全珍第一次見(jiàn)到甘祖昌。那次,校長(zhǎng)李平讓她給時(shí)任新疆軍區(qū)后勤部長(zhǎng)的甘祖昌匯報(bào)后勤部子弟們的表現(xiàn)。
等甘祖昌走后,李平對(duì)龔全珍說(shuō):“甘祖昌是個(gè)思想意識(shí)很純潔的老同志,他也受過(guò)痛苦婚姻的折磨,離婚了,這點(diǎn)你們有相似的遭遇。我給你們介紹認(rèn)識(shí)。我相信你們的思想感情會(huì)融洽的。”
龔全珍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:“他是個(gè)大首長(zhǎng),這點(diǎn)不合適。我見(jiàn)首長(zhǎng)就不會(huì)講話,受拘束。”
龔全珍老人回憶說(shuō),她腦子里像開(kāi)了鍋的水似的,翻來(lái)覆去不能入睡,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。
那一年放寒假,龔全珍和老師們到后勤部子弟家家訪。甘祖昌和大伙兒一道用餐,她第一次看清他的樣子。甘祖昌一米七多的個(gè)子,因?yàn)槭荩燥@得高;方臉,滿臉嚴(yán)肅;眼睛不大,卻很銳利;身板筆挺,標(biāo)準(zhǔn)軍人姿態(tài)。
飯后老師們返校了,甘祖昌和龔全珍進(jìn)行長(zhǎng)談。
“我今年48歲,校長(zhǎng)告訴過(guò)你吧?”甘祖昌問(wèn)她。
“好家伙,如此坦率干脆!開(kāi)門(mén)見(jiàn)山,比我大18歲。”龔全珍心想。
甘祖昌接著告訴龔全珍,他的身體不好,有腦震蕩后遺癥,還有氣管炎、肺氣腫。原來(lái),新疆和平解放后,甘祖昌在一次外出檢查工作時(shí),敵特分子截?cái)嗔四緲颍俗募哲?chē)從橋上栽下。甘祖昌頭部重傷,落下嚴(yán)重的后遺癥。
龔全珍被甘祖昌的革命經(jīng)歷所震撼,也被他的坦誠(chéng)所打動(dòng)。通過(guò)這次交談,她不僅了解了甘祖昌個(gè)人及家庭情況,更了解了他為人處世的態(tài)度。
沒(méi)有過(guò)多的花前月下,沒(méi)有過(guò)多的甜言蜜語(yǔ),只有相守終身的信念。兩人的婚禮在一個(gè)小會(huì)議室舉行,只擺了兩桌簡(jiǎn)單的飯菜,大半的客人都是同事。
起初,有同事?lián)模粋€(gè)連“龔”字都寫(xiě)不出,一個(gè)是鐘愛(ài)《簡(jiǎn)·愛(ài)》的大學(xué)生,能有共同話語(yǔ)嗎?
一天飯后,夫妻倆一起坐在樹(shù)蔭下學(xué)習(xí)《毛澤東選集》。
文化水平不高的甘祖昌給妻子介紹起《井岡山的斗爭(zhēng)》,解釋什么叫主觀主義,教她讀懂革命這本無(wú)字書(shū)。龔全珍則給丈夫講解某個(gè)字詞的讀法、詞義、用法。
對(duì)于自己和甘祖昌的愛(ài)情,龔全珍曾在日記中這樣評(píng)價(jià):“在我的腦海中,愛(ài)情有3種境界:最高境界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標(biāo),愿為之奮斗終生,不惜一切代價(jià)甚至生命的愛(ài)。我和祖昌共同生活33年……我感到生活得充實(shí)幸福。”
“要挑老紅軍的擔(dān)子,不擺老干部的架子”
“他為什么不吃好的,不穿好的,他心里常常想著為革命犧牲了的戰(zhàn)友,要多奉獻(xiàn),少享受,要為建設(shè)家鄉(xiāng)貢獻(xiàn)出一切。”
——摘自1992年9月28日龔全珍日記
崇拜三哥,龔全珍走上探尋革命真理之路。在丈夫身上,龔全珍則讀懂了一個(gè)真正的共產(chǎn)黨員。
1957年6月,龔全珍從甘祖昌口中聽(tīng)到一個(gè)令她震驚的消息,甘祖昌決定帶全家人回江西老家,不當(dāng)將軍當(dāng)農(nóng)民。
彼時(shí)的甘祖昌已被授少將軍銜,一家人也早已習(xí)慣了新疆的生活。聽(tīng)到丈夫這番話,龔全珍輾轉(zhuǎn)難眠,她翻了翻丈夫的日記本,里面夾了3張請(qǐng)求回鄉(xiāng)勞動(dòng)的申請(qǐng)報(bào)告,從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張。
這些報(bào)告的內(nèi)容都一樣,上面寫(xiě)著:“自1951年我跌傷后,患腦震蕩后遺癥,經(jīng)常發(fā)病,不能再擔(dān)任領(lǐng)導(dǎo)工作了,但我的手和腳還是好的,我請(qǐng)求組織上批準(zhǔn),我回農(nóng)村當(dāng)農(nóng)民,為建設(shè)社會(huì)主義新農(nóng)村貢獻(xiàn)力量。”
龔全珍擔(dān)心甘祖昌頭部受傷,老家的醫(yī)療條件無(wú)法保障。回鄉(xiāng),也意味著重新開(kāi)始,更何況到艱苦的農(nóng)村去。對(duì)此,同事、朋友紛紛勸說(shuō)。可是,甘祖昌去意已決,龔全珍也決意相隨,“我們有共同之處,對(duì)生活要求不高,為理想可以貢獻(xiàn)出一切”。
準(zhǔn)備動(dòng)身時(shí),甘祖昌向全家發(fā)布了一道命令:不準(zhǔn)帶棉花。
“棉被棉衣只帶面。國(guó)家沒(méi)有那么多差旅費(fèi),路這么遠(yuǎn),路費(fèi)比買(mǎi)新棉花還貴。”甘祖昌說(shuō)完,仔細(xì)檢查一家老小的箱子和麻袋,檢查完才讓捆好。
經(jīng)過(guò)半個(gè)多月的旅途,一家人終于回到甘祖昌的江西老家——蓮花縣坊樓鎮(zhèn)沿背村。
從將軍到農(nóng)民,對(duì)甘祖昌來(lái)說(shuō),是身份和心靈的回歸。
當(dāng)年,他為了解放勞苦大眾,告別母親和家鄉(xiāng),走上革命道路。長(zhǎng)征路上,他和同村戰(zhàn)友約好,革命成功后,一起回家搞建設(shè),讓鄉(xiāng)親們過(guò)上好日子。
回家才兩天,甘祖昌就領(lǐng)著子女下地干活。“要挑老紅軍的擔(dān)子,不擺老干部的架子。”甘祖昌處處用紅軍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(tǒng)要求自己,他希望能和鄉(xiāng)親們一起努力改變家鄉(xiāng)的落后面貌。
他親自下田,用雙手一抔一抔撈爛泥,帶領(lǐng)鄉(xiāng)親們把200多畝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;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,和年輕人一起挑水泥、運(yùn)材料,修建起了江山陂……
將軍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,龔全珍踏入的卻是一個(gè)完全陌生的世界。完全聽(tīng)不懂當(dāng)?shù)胤窖缘凝徣湟粋€(gè)人步行40多里路,到縣文教局毛遂自薦當(dāng)老師。
在學(xué)校里,面對(duì)山村里的學(xué)生,龔全珍是既當(dāng)老師,又當(dāng)媽媽?zhuān)患纫趟麄冏x書(shū),還要帶他們勞動(dòng)。
看到別人家里每天父母孩子都能熱熱鬧鬧在一起,女兒甘仁榮就問(wèn)父親:“為什么你們不能像別人家的爸爸媽媽那樣陪著我們?”
父親若有所思地說(shuō):“因?yàn)槟銈兊膵寢屖菍W(xué)生娃的媽媽?zhuān)銈兊陌职质寝r(nóng)業(yè)社的爸爸。”
甘仁榮和兄妹們聽(tīng)到父親這番回答,大眼瞪小眼無(wú)法理解,甚至還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他們親生的。
甘祖昌每月工資330元,收入水平在當(dāng)時(shí)很高,但一家人卻都過(guò)著簡(jiǎn)樸的生活。僅當(dāng)?shù)剜l(xiāng)政府不完全統(tǒng)計(jì),將軍回鄉(xiāng)后參加建設(shè)了3座水庫(kù)、4座電站、3條公路、12座橋梁、25公里長(zhǎng)的渠道。有統(tǒng)計(jì)的捐款達(dá)8.578萬(wàn)元,占他全部工資的70%。
將軍對(duì)群眾如此“大方”,但是對(duì)自己和家人卻很“吝嗇”。家人的衣服破了就補(bǔ)好再穿,實(shí)在不能補(bǔ)了拿去做鞋底。“只能給后代留下革命傳家寶,不能留下安樂(lè)窩。”這是甘祖昌常對(duì)子女講的話。
兒子甘新榮本來(lái)有當(dāng)兵的機(jī)會(huì),甘祖昌說(shuō)招兵名額有限,讓他留在家鄉(xiāng)務(wù)農(nóng)。
大女兒甘平榮也從小想當(dāng)兵,甘祖昌不僅沒(méi)有出面幫她,甚至告訴了吉安軍分區(qū)的領(lǐng)導(dǎo)同志她的右眼近視,希望嚴(yán)格把關(guān),這番話當(dāng)場(chǎng)把女兒氣哭。
龔全珍從教育工作崗位退休時(shí),小女兒甘吉榮打算去學(xué)校“頂班”,也遭到甘祖昌的堅(jiān)決反對(duì)。
……
在關(guān)系兒女人生前途的大事上,甘祖昌的不近人情曾讓子女們哭鬧過(guò)、埋怨過(guò),但隨著兒女閱歷的增長(zhǎng),都化為從善、獨(dú)立、有愛(ài)心這些美好的品格。
“父母雖然沒(méi)有給兒女房產(chǎn)和金錢(qián),卻把無(wú)限的精神財(cái)富給了后代。”甘仁榮說(shuō),這些年來(lái),大家都在獻(xiàn)愛(ài)心、做善事,盡自己所能,傳遞這份愛(ài)。
“活著就要為國(guó)家做事情”
“我走過(guò)的路崎嶇、艱難。我一直過(guò)著清貧的日子,可是我沒(méi)有遺憾,沒(méi)有悔恨,心懷坦蕩。只要過(guò)寧?kù)o、簡(jiǎn)單的生活就滿足了。”
——摘自1989年3月26日龔全珍日記
1986年,甘祖昌將軍永遠(yuǎn)地離開(kāi)了。彌留之際,他交代老伴:“領(lǐng)了工資,買(mǎi)了化肥農(nóng)藥,送給貧困戶。”
除了這句遺言,甘祖昌并沒(méi)有給家人留下什么,他幾乎所有的錢(qián),都用在了農(nóng)村建設(shè)上。丈夫一心為公、無(wú)私奉獻(xiàn)、艱苦奮斗的寶貴精神,也成為龔全珍的人生信仰。
家鄉(xiāng),還有著丈夫未竟的事業(yè)。“老伴,你到另一個(gè)世界去了,我還要在這個(gè)世界上,繼續(xù)我的征程。”
快70歲時(shí),龔全珍主動(dòng)提出住進(jìn)蓮花縣幸福院,要去那里照顧比自己年長(zhǎng)的老人;她著手做社會(huì)調(diào)查,到各鄉(xiāng)鎮(zhèn)調(diào)查青少年失學(xué)情況,參與成立關(guān)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(huì);她成立“龔全珍工作室”,捐資助學(xué),扶貧濟(jì)困,服務(wù)社區(qū)……
“我不能庸庸碌碌過(guò)日子,應(yīng)以戰(zhàn)斗的姿態(tài)向死神挑戰(zhàn);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淪,要抽出主要時(shí)間來(lái)工作。”這是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記中的一句話。2013年,老人又在日記中寫(xiě)下:“一個(gè)共產(chǎn)黨員要為實(shí)現(xiàn)中國(guó)美好的夢(mèng)做點(diǎn)事,為社區(qū)的建設(shè)盡點(diǎn)力,不能等死。”
后來(lái),即使躺在病床上,龔全珍也總會(huì)督促兒女們下鄉(xiāng)走訪,去了解誰(shuí)家有人生病看不起、誰(shuí)家孩子上大學(xué)缺學(xué)費(fèi),要求他們一家一家上門(mén),把關(guān)心送到對(duì)方手中。
幾十年來(lái),沒(méi)有人記得她去過(guò)多少學(xué)校,幫助過(guò)多少人。但記者曾不止一次看到,老人外出參加活動(dòng)吃飯時(shí),拿出自帶的饅頭或面包啃。她說(shuō):“我牙齒不好,吃這個(gè)好。”
在甘祖昌、龔全珍的影響下,兒孫們盡管身處平凡崗位上,卻個(gè)個(gè)品行端正、工作敬業(yè),有的獲評(píng)“全國(guó)三八紅旗手標(biāo)兵”,有的榮膺“全國(guó)勞動(dòng)模范”。
同事和朋友曾送給甘家子女16個(gè)字:革命后代,將軍傳人;淡泊名利,情操高尚。這既是對(duì)甘祖昌和龔全珍兒女們的褒獎(jiǎng),更是對(duì)這個(gè)革命家庭高尚家風(fēng)的贊揚(yáng)。
多年來(lái),龔全珍始終踐行著丈夫當(dāng)年的那句話——“活著就要為國(guó)家做事情,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,干不了復(fù)雜重要的工作就做簡(jiǎn)單的工作,絕不能無(wú)功受祿,絕不能不勞而獲。”
龔全珍鐘愛(ài)荷花,愛(ài)它的不蔓不枝,皎潔無(wú)瑕,奉獻(xiàn)一生。
其人如荷,清香滿人間。(記者 賴(lài)星)